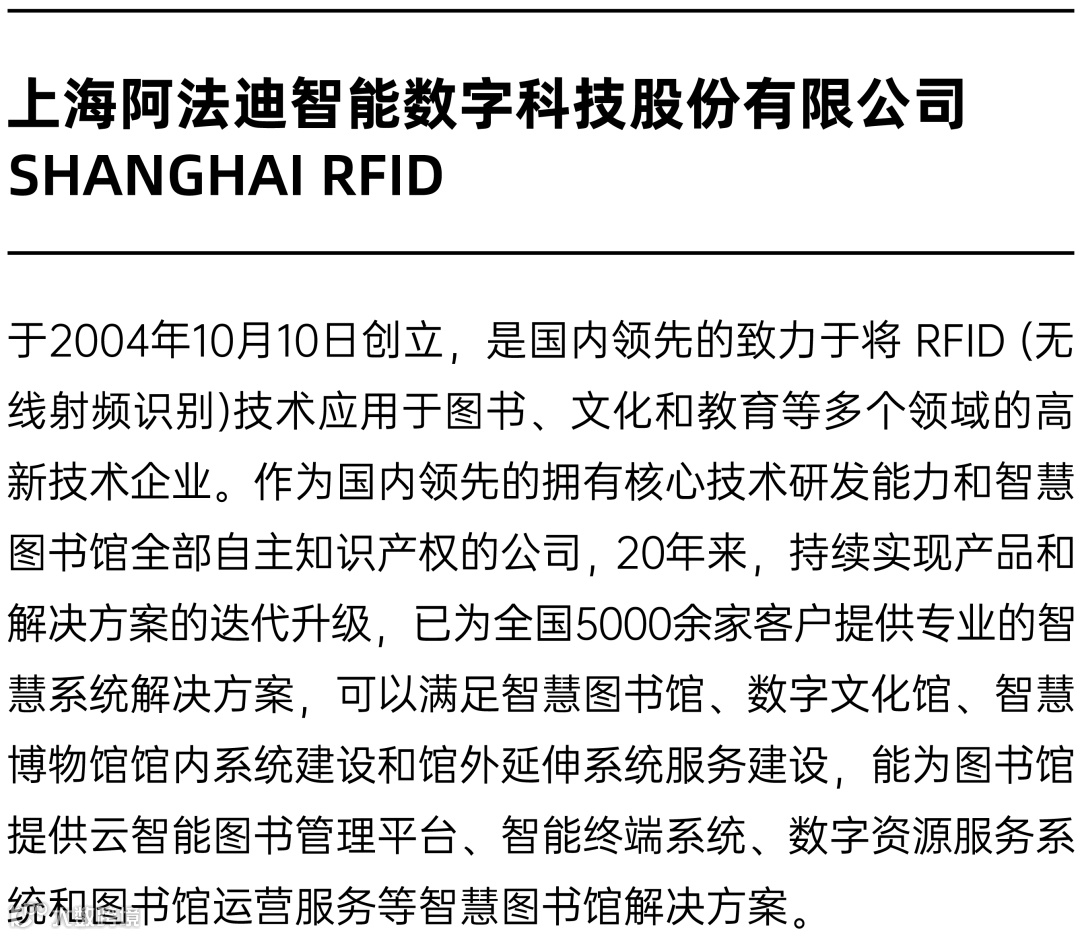电视剧《繁花》的上映,带火了黄河路和上海美食。汪小姐至爱的排骨年糕,外卖搜索量猛涨7倍,老字号“鲜得来”云南路总店史上头一遭卖空了。火锅热气蒸腾,见证了阿宝的缘起缘灭。观众们追得津津有味,边看边点菜。
作家们喜欢用食物隐喻世间万物,哲学家也这么认为:“人就是他所吃的什么”。人之为人,与他的食物、获取食物的渠道、享用食物的方式,关系匪浅。

王安忆:上海小姐的食色
《长恨歌》写的是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人人都认定王琦瑶就是上海,上海就是王琦瑶。
至于上海究竟是美丽还是小资、是虚荣还是聪慧、是风情还是小布尔乔亚的纸醉灯迷莺歌燕舞,那就是见仁见智了。
王琦瑶天生丽质难自弃,因此当选“上海小姐”。乱世名媛,做了权贵的金丝雀。事后看当然是不值得。但身处其间,还是迷失在海上繁花之中。
金屋的日子静极生闲,还好她没有染上恶习、恶疾。此后沧桑巨变,金主死于逃难,她也搬出金屋回到市井。
中年王琦瑶最爱吃泡饭加黄泥螺。其实黄泥螺也蛮好吃的,但终究不是活色生香的正餐。
弄堂里的生活和人情都是素净的。
隔壁的严家师母叫她打牌,会准备好王家沙或者乔家柵的点心。围炉而坐,还滋生出一股类似亲情的气氛。
临近过年,她们一人一把汤匙在炉上做蛋饺,把做好的蛋饺一圈圈排在盆里,排出花朵和宝塔的样子。王琦瑶在炉边用一盘小磨磨糯米粉。萨沙自告奋勇往磨眼里舀米,半勺水半勺米的。毛毛娘舅摇磨,王琦瑶则用石舂舂芝麻,严师母什么也不做,只在嘴里发指令。
蛋饺、米糕,都是沪上最家常的食物,作者却写出了细腻的人情。
王琦瑶偶尔下厨整顿饭招待客人:“事先买好一只鸡,片下鸡脯肉留着热炒,然后半只炖汤,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鸭,剥几个皮蛋,红烧烤麸,算四个冷盆”。 热菜是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
这桌菜,用作者的话说是“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菜,没有一点要盖过严家师母的意思,也没有一点怠慢的意思”。
看在外人眼里,这一桌冷盆、热炒,颜色漂亮,荤素、浓淡调停得当,兼顾了制作成本和时间的统筹。看似波澜不惊,却极有用心,真真是一个上海女人的作为。
当事人的感受自然更深: “起了热锅以后,王琦瑶还眼中含泪,觉得今天终于热气腾腾,活过来似的。煤炉上炖着鸡汤,她另点了只火油炉炒菜,油锅哔剥响着,也是活过来的声音”。
终其一生,她找不到一人可长久共一桌家常茶饭。

张爱玲:文艺女青的心水
张爱玲说自己就是个俗人,所以她讲了很多花开花谢的故事,也喜欢絮叨她喜欢的衣服和食物。
张爱玲吃东西很刁,哪怕是吃螃蟹面,她也是“吃掉浇头,把逼干了就放下筷子,自己也觉得有点造孽”。
张爱玲对西点也有严格的评分,特别点名表扬自家隔壁那家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而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
张爱玲喜欢他家特有的“方角德国面包”,说外皮厚脆中心微湿,是“普通面包中的极品”,并且引用姑姑张茂渊的话“可以不抹黄油,白吃”。 她还曾买大盒的奶油蛋糕准备送人,因为“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
飞达咖啡馆则是张爱玲的乡愁。晚年侨居国外,还念念不忘:“加拿大的香肠卷从手艺上比不上以前上海飞达咖啡馆的名厨,油大又辛辣”、“纽约一家丹麦人开的点心店里,拿破仑比不上飞达的好”……
留恋的不仅是口味:“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拣,他自己总是买香肠卷。”
虽然她早就与他那个抽大烟又续娶的父亲断绝了关系,但那血缘深处的羁绊却是斩不断理还乱的。
四十年代后期,物价疯狂上涨,很多咖啡馆西点店都难以维系原来的水准,飞达的栗子蛋糕还能保持一贯水准。当然价格也是贵的。大家一边吃,一边称赞:“贵虽贵,生意还是好的,一出笼便卖完了,迟到一步便尝不到了”。
飞达持续到1950年代结束营业。据说蛋糕师傅被凯司令请去,所以那栗子粉蛋糕的味道一如既往地好,历经九十余年的时光,至今仍是招牌。
上海人确实是喜欢咖啡馆的。
上海的咖啡馆首先是个社交场所。其意不在咖啡,至少不专在咖啡。凸显的是社交和事务功能。
见朋友、谈事情、谈生意,约会,然后才是咖啡和蛋糕。
据说张爱玲就喜欢在咖啡馆写作,静安区特意开了家“玲咖啡”向她致敬。
这里也是“张迷”的朝圣地。咖啡馆布置成老上海格调,有怀旧墙纸和张爱玲旧照。书架上放着老上海和张爱玲的书。普通“张迷”来喝咖啡兼拍照,陈子善之类的知名“张迷”则喜欢带人来这里开派对。

鲁迅:文化巨擘的宴席
夏丏尊曾回忆道:“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是鲁迅每夜必需的粮,斋夫摇寝铃前买好送进房间,周六夜里备得更富足”。
鲁迅夜夜吃条头糕,竟然不腻,果然是国产糯米胃。
但鲁迅是文坛巨擘,私下可以吃得恣意,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讲究排场的。比如他招待英国文豪萧伯纳,午饭甚至都开在了宋庆龄的家里。
鲁迅又常组织活动,所以他可以穿得马马虎虎,但请客吃饭却一点都不吝啬,也因此对沪上的饭店如数家珍。
被鲁迅翻过牌子的饭店包括:新雅粤菜馆、功德林、新亚饭店、知味观、南京饭店及荷兰西菜室等。
在功德林和田汉等进行文艺漫谈;在荷兰西菜室和左翼团体聚会,还过了自己的五十岁寿辰;在新雅茶室等地和陈望道等商谈杂志编辑……
其中知味观是鲁迅在上海期间去得最多的地方。1933年,一年内就在知味观请客五次:4月22日晚,“在知味观招诸友人夜饭,坐中为达夫等共十二人”,这次宴会是为了介绍姚克与上海文艺界人士见面,同时也为郁达夫践行。10月23日,宴请日本福民医院院长和内山君等,点了“叫化鸡”、“西湖莼菜汤”等。日本人回国后,广泛宣传知味观,以致很多年后,日本团体到上海访问时,还对照着书寻到知味观来吃饭。
名人是菜馆最好的广告。汪伦请李白喝顿酒,就因此而青史留名了。饭店的老板们也深谙此理。
比如汉口路云南中路的豫菜名楼——梁园致美楼。老板是河南开封人岳秀坤,他知道鲁迅是沪上名人,每次鲁迅到梁园吃饭,他鞍前马后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主动上门给鲁迅做家宴。鲁迅也没辜负老板的心意,把他写进了日记里:“晚熟梁园豫菜馆来寓自馔”。
1934年,鲁迅曾5次在梁园请客,每次必点糖醋软熘鲤鱼焙面。特别是宴请萧军、萧红那次,鲁迅钦点了鲤鱼焙面、炸核桃腰、三鲜铁锅蛋、酸辣肚线等。此后这个席面便被命名为“鲁公筵”。
而梁园致美楼也正如老板所愿,和鲁公一起永远地留在了现当代文学史那一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