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曾以《第三次浪潮》享誉全球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因病去世,1983年托夫勒带着这本书首次来华,《第三次浪潮》对中国带来哪些影响?这个事件与后来中国发起的新技术革命对策研究有什么关系?我们特邀请中国科技情报领域的领军学者、也是那次事件的参与者缪其浩研究员撰文回顾这段往事。

"人们跑来告诉我,他们记得曾经骑车十几公里去观看‘第三次浪潮’电视片"
托夫勒: 2006年接受《人民日报》英文版采访时的讲话[1]
我目前所在的办公室多年前曾是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大礼堂的一部分。这个大礼堂经常为专业人员播放国内外的科技影片,通常观众不少但一般不会很热闹。但33年前曾有一段时间,我记得这里却是天天门庭若市,直到最近还会有那时的观众向我提起到情报所看片的“轶事”。那次播放的片子题为“第三次浪潮”,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片,而是反映未来趋势以及它将怎样影响世界的,今天这类信息已经太多、甚至可能有点滥了,而在那时却还非常罕见。

图一,阿尔文•托夫勒及其《第三次浪潮》
(图片来自网络)
这部片子的原版,是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带来的。他于6月27日以87高龄去世。尽管近年来因年龄关系他不再活跃,中外媒体还是没有忘记他对“未来学”从偏门变成显学所作的贡献。作为一位文科背景的记者,他对信息技术许多方面后来几十年发展做出的准确预测令人惊讶,这可能与他曾经为IBM等信息技术巨头做过多项研究有关;然而他又并非狭义上的“技术预测”专家,其主要贡献在于预见并提醒社会,新技术将可能带来各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媒体上所有回忆文字必提的是那几本畅销的名著。其成名作是《未来冲击》,而传播更广的则可能是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尽管现在类似的论述和专著可以说连篇累牍,这本书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就在托夫勒去世前不久,曾是美国最大互联网公司“美国在线(AOL)”的创始人之一的凯斯就将他一本新书取名为《第三次浪潮》,表示这是向托夫勒致敬。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托夫勒又与中国有过一段特别的缘分,2006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将其列入近几个世纪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50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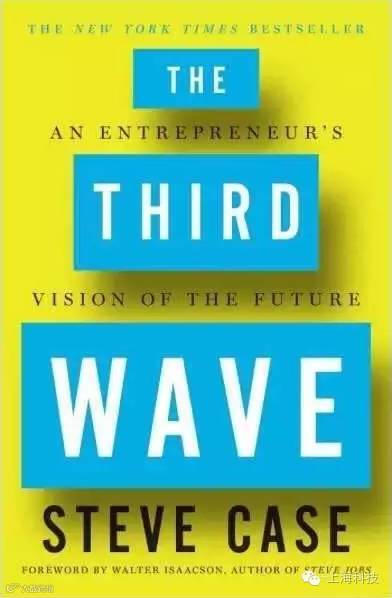
图二,Steve Case:The Third Wave,Simon & Shuster,2016年5月
然而在他1983年初首次访华前,中国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第三次浪潮,即使嗅觉灵敏的《读书》杂志1981年11-12期刊登了董乐山编译的“托夫勒的‘三次浪潮’论”,影响也不大。而他也只是在自己的《第三次浪潮》出版两年多才想到访华。但是有些事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983年1月2日,托夫勒夫妇应中国未来研究会邀请首次访问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关于这个“浪潮”的学术报告。托夫勒在华期间先后会见他的包括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社会科学院顾问宦乡、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等重要人物,在上海访问时还受到市长汪道涵的接见。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有点“偏门”的学者得到如此的接待规格?
1983年时文革已经结束数年,虽然“小岗村”撕开了计划经济的一道口子,市场化改革仍然困难重重;处理了四人帮及其爪牙、许多干部“官复原职”,恢复文革前的轻车熟路符合“最小阻力原理”,所以局面一旦大致稳定,改革的动力就明显不足了。而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复杂程度相比,发展科学技术是最没有争议的,被誉为科学春天信号的“全国科学大会”就在1978年3月召开,9个月以后才有对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性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0年12月,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首先就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提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实现战略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通过科学技术来推动全面的改革和发展的“路线图”。所以中国科技界甚至更高领导层关注世界新技术发展及其带来的可能机会和冲击,我感觉正是想借助这样一种社会有较多共识的外部推动力。而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此时此刻正好成为送上门来的机会,我觉得这是这位未来学者在国内引起如此重视的原因。
2006年接受《人民日报》英文版采访时托夫勒提到的“‘第三次浪潮’电视片”,我有很大的把握说那并不是他的原版作品,而是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整理编辑的中文版。因为原版不仅是英文的,而且包含个别很不适宜的画面,来华后仅在几次小范围的专业交流活动上播放过。后来广泛传播的那个版本是上海编辑制作的,这就是我想说的托夫勒访华中的上海故事。
80年代是上海科技界思想非常活跃的年代,软科学可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崛起,在国内占据重要地位。当过一机部情报所领导的老市长汪道涵对世界科技经济新动向的关注早为人津津乐道。上海市科委那时有个预测处,布局全市的科技政策研究,还包含了产业和经济研究的课题研究。情报所持续性的动向跟踪就是在预测处领导下进行的。继北京之后上海成立了未来学会,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也在1980年建立,幕后英雄是后来当过市委组织部长的所长周克,而前台则涌现出冯之浚、刘吉那样的软科学领域明星人物。
托夫勒来上海除汪市长接见外,上海市未来学会组织了场报告会,情报所研究室马远良和简报室苏光楣参加报告会后意犹未尽。长期为领导科技决策服务养成的敏感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题材值得进一步挖掘。经过领导批准后,通过未来学会邀请托夫勒到情报所举行一次深度的交流和研讨。在那个时期,上海市科委的对外交流中心就挂在情报所名下,在外商来沪举办商品和技术展览期间组织“技术座谈”是标准程序,即使文革期间也没有完全中断。具体主要是由情报所人员操办,所以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与北京的活动许多大人物出场不同,这次座谈前,情报所张秀副所长只是来握了握手表示欢迎就离场了,留下一场相当专业的小型座谈(图三)。
座谈场所虽简陋,说“专业”却一点不夸张。其一参加人员多为资深研究人员,多年跟踪国际科技和产业发展动向。上海情报所购买外国科技资料的资金有好多年是全国第一的,文革时期因属于“内部单位”资料免于遭劫。情报所收集除学术文献外,还包括相当多的技术和行业资料,后来还可以远程访问一些数据库。所以我们对第三次浪潮所处的时代背景、其中的高科技和新兴产业是有所了解的,在座谈前我们还设法搞到了一本原版《第三次浪潮》,进行了一些预习;其二,现场安排了翻译。实际上她很空闲,因为参加者基本上能与托夫勒直接交流,干情报这行应该清楚,“魔鬼”常常就在跨语言的细节中。
我当时在情报所就读研究生刚满一年,有幸坐在第二排参加了座谈。年纪不小“辈分”很低,但也有发声音的机会。我发言提到有本《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问托夫勒它和第三次浪潮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让他很兴奋,引出了很长一段回应,最后还问我是不是在美国读过书,其实那时我还没有任何出国经历。我记得托夫勒提到“浪潮”这个词来源于美国历史上西部淘金热时期的一个说法,也是3个W, West Ward Wave;还有个细节是托夫勒的太太海蒂在座谈中非常活跃,可称得上“夫唱妻随”,因为那本《第三次浪潮》实际是两人的合作产品。据一位参加座谈的老同志回忆,托夫勒当时说过上海的这次座谈是在中国搞得最好的,从我现场感受到的气氛来看,这个判断是靠谱的。

图三,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座谈会。照片左侧为托夫勒夫妇;右侧中间服装颜色略淡者为马远良,他后来是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照片由马远良提供)
前面提到过的影视片就是此次座谈的重要成果之一。托夫勒同意我们以他带来片子为原本制作一部中文片子,不收任何费用,只是要求不对外公开放映。我们为什么要制作中文版?一来托夫勒的影视片原是面对西方读者的。对大多数刚刚经历文革、与外部世界接触甚少的中国受众来说并不易懂,其中不完全是语言问题,有些表达方式中国受众不习惯;其次,或许是更加重要的,我们需要在尊重原作者基本观点和大量宝贵素材的前提下,尽可能用我们的叙事方式来讲述第三次浪潮,让它不仅起到开眼界的作用,而且能够启迪我们自己怎么做的思考。在技术上,情报所本来就有个科技影视制作部门,外语人才也没有问题。事实证明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中文版制成后立刻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仅在上海就放映了176场,观看者多达23万人次[2],观众已经远不止科技人员,还包括政府官员和其他机构人员。刘振元副市长在听取情报所汇报后安排该片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厅为市领导放映,后来该片还传到了北京和兄弟省市,影响遍及全国。
然而对高层决策发挥更大影响的倒并不是这些浮在面上的东西。在座谈以前,情报所简报室就已连续编写内部简报,是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来描述第三次浪潮,并且提出了对策建议。简报得到了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领导的肯定。影视片播放后情报所几位资深研究人员纷纷受邀到一些专业机构做报告,不仅是介绍第三次浪潮,而且结合自己的跟踪研究,让人们进一步认识新技术正在如何改变着世界,更加重要的,是启迪了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思考;现在来看,这些工作实际上也为不久以后中国科技发展一个重大事件做了舆论的准备。
1983年10月中央发起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和我国的对策研究。
10月28日胡耀邦总书记批示,肯定了追求新的现代化科学知识,并且把这些新知识同如何改变我国现状联系起来的做法。11月1日马洪组织了对策研究小组,发起了全国大讨论,而《第三次浪潮》、《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等则成为大讨论中的重要参考材料,各种中译本印数达数百万册。大讨论直接参与者多达2000余人。对策研究成果累累,包括8个专题的各种研究报告,以及汇报提纲和对策建议等重要文件。863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就是对策研究的直接结果,现在我们熟知的新兴技术产业几个重大领域也是在当时聚焦。今天中国科技可以自豪地站在世界前列,那场大讨论和对策研究功不可没!
而上海在大讨论和对策研究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上海是除北京外中央唯一指定建立研究小组的。1983年12月成立的“新技术革命和上海战略对策”研究课题组由冯之浚任总组长,马远良、夏禹龙[3]等四人任副总组长,大量成果为上海市以后的科技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国家战略的形成做了贡献。后来国家科委领导来上海,专门到情报所看望了简报室的同志,称赞他们“办了一件好事,不仅影响了上海市的某些战略决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战略决策”。顺便提一下,我的硕士论文研究课题有幸列入了市科委对策研究的重大项目,虽然没有经费,但有机会为此做了些微工作。
与几十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波澜壮阔相比,这里记录的只能算一朵浪花而已,但是其中有关科技人员体现出来可贵的责任意识和主动精神,领导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以及敢于担当不怕犯错误的可敬态度应该永远被铭记。
本文许多细节参考了以下文章:
柳红:记1984年关于迎接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全国性讨论,经济观察报,2014年10月24日
江世亮:“指兔子”,缺不得“职业团队”,文汇报,2012年6月15日
写作前还访问或电话采访了参与当时活动的老同志,包括马远良、朱南如、苏光楣和沈彩虹等,深受感动、深表谢意!
1, 转引自《环球时报》英文版2016年6月30日
2, 数字引自的《情报的回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一书中沈彩虹所著“点燃新技术革命之火”文章(127页)
3, 冯之浚、夏禹龙、张念椿和刘吉被并称科学学所“四条汉子”,是全国软科学界早期的领军人物
缪其浩,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原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是中国科技情报领域的重要领军人物。
来源:三思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