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的经典名著《西方宪政体系—美国联邦宪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章第1节。
在美国独立之时普通法虽然抛弃了对出版的事前审查,但仍然保留煽动诽谤法对有害言论的事后追究。独立后的各州政府继承了英国普通法——包括它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例如在1735年的贞格案(Zenger Case),纽约州指控出版商贞格犯有煽动诽谤罪。法院并不接受作品确实性的法律辩护,但陪审团罔顾了当时的法律,方使被告获得无罪释放。

在1788年批准宪法之后,各州又于次年通过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中第1修正案明确禁止国会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但在此后一个多世纪内并未限制各州政府。尽管麦迪逊认为简单列举受到普遍承认的原则,将使修正案轻易获得通过,对第1修正案的解释远比想象复杂。法学界历来持有两种观点:保守的解释认为,第1修正案仅明确取消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事前限制”(Prior Restraint);更为激进的解释则坚持这项修正案具有双重目的,不但取消了事前限制,而且禁止对煽动诽谤的指控。



例如切菲(Z. Chaffee)教授在40年代指出:“第1修正案起草者和批准者的中心意图,乃是取消普通法的诽谤法,并只要个人不鼓动违法犯禁,它永远禁止在合众国内对政府批评进行指控”。
近来的历史研究表明,虽然杰弗逊和麦迪逊等缔造者曾提倡过广义解释,第1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使各州——而非联邦——获得调控言论的立法权力。因此,第1修正案似乎并不要求取消当时普遍存在的煽动诽谤法。


直到1907年,霍尔姆斯法官(J. Holmes)仍然重复布莱克斯通的评论,认为“宪法条款的主要目的,乃是禁止其他政府对出版所行使的所有事前限制——而非对抵触公共福利的出版所实行的事后惩罚。”十多年之后,他才改变了这种观点。

在建国之初,国会对言论的严格控制,表现在恶名昭彰的《排外与煽动法案》(Alien and Seditious Act)。1798年,当时控制政府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s)通过这项法案,来迫害反联邦的杰弗逊党人(Jeffersonian)。


它规定:“任何人不得书写、印刷、谈论或发表…任何错误、毁谤和恶意中伤的作品,来反对合众国、国会两院或总统,并企图诽谤他们、或使之名誉扫地、或激起合众国良民反对政府的仇恨、或在合众国内煽动叛乱、或任何以上违法行为的组合,以反对或抵制合众国的人和法律或其总统的任何合法行动……违者犯法”,并将受到5000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法案允许被告通过证明确实性进行辩护,并规定陪审团同时决定法律和事实。尽管具备这些限制,法案还是受到杰弗逊和麦迪逊的联合攻击,并被指责为公然违宪。
在1798年著名的“弗吉尼亚决议”(Virginia Resolution),州议会决定(选译自纽约时报诉沙利文(New York Times v.Sullivan, 376U.S. 254)):
[议会]特别抗议最近两个“煽动法案”案例对宪法的明显侵犯。[煽动法案]所行使的权力缺乏宪法委托授权;相反,它受到第1修正案的明确和正面禁止。这项权力应该引起普遍警惕,因为它所针对的权利,不仅是检查公共事务和措施的自由,也是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自由;这些权利一直被公正地认为是所有其他权利的惟一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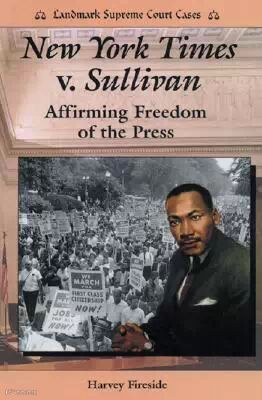
麦迪逊准备了支持这项抗议的报告。他的基本前提是:在宪法创造的政府形式下,“人民而非政府掌握着绝对主权。”他在早先的众议院辩论中说道:“如果我们留意共和政府的性质,那么我们发现审查权力在于人民针对政府,而非政府针对人民”。对于报社所行使的权力,麦迪逊的报告指出:“对每一件事物的正当使用,乃是和某种程度的滥用分不开的;这对新闻来说是再正确不过了。几乎在联邦的每一州,报社行使自由去检查形形色色公众人物的政绩和措施。。。因此,各州实践已经决定,与其修剪毒苗而伤害正当果实的茁壮成长,还不如任由它们生存和繁殖”。在麦迪逊看来,自由批评公共官员的权力,乃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

《反煽动法案》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弹。部分由于利用这项法案所进行的迫害行为,联邦党人终于声名狼藉,并在选票箱前败给了其政治对手。
1800年,杰弗逊总统上任后,立即对所有被法案定罪的个人实行大赦,并给予政府赔偿。次年,《反煽动法案》自行过期、无疾而终。政治迫害使杰弗逊党人突破了普通法对言论自由的传统观念。他们提出,自由政府要求自由的政治讨论,并只要不发生有害的实际行为,言论不应受到刑事惩罚。但对第1修正案本身,杰弗逊党人对联邦主义和各州权力的考虑,终究胜过对自由言论的热爱。在控制总统和国会权力之后,他们对政治批评似乎并不比联邦党人宽容多少。

1806年,康涅狄格州的两名编辑因针砭总统和国会,而在联邦法院受到普通法诽谤罪的指控。最高法院因联邦不具备普通法刑事管辖权——而非第1修正案对言论的普遍保护,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定罪(UnitedStates v. Hudson & Goodwin, 11 U.S. 32, 1182.) 。

在《反煽动法案》的风波平息后,国会在整个19世纪并未制订人和法律去严重约束言论自由。执法和司法机构曾对言论实行过有限程度的控制。例如1789年的《法院组织法》(Judiciary Act),即授权联邦法院惩罚“所有对法院诉讼和听证权力的蔑视行为”;联邦法院一度利用惩罚蔑视法院的权力(Contempt Power),去禁止公民对法院决定的批评。

1835年,南部的奴隶主希望平息反蓄奴主义者的抗议。杰克逊(Jackson)总统建议国会通过法案,禁止煽动奴隶暴动的邮件在南部流通。


国会领导人卡尔宏(Calhoun)起初表示反对,后来却提议通过法案,禁止地方邮政局长接受或传递任何讨论蓄奴制的邮件。尽管这些法案均未获得通过,邮政局长们在地方压力下曾拒绝邮递反蓄奴的邮件。

1863年,美国处于内战前夕。联邦邮政部长行使权力,清除或拒绝邮递反对联邦的文件或资料。最后,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和军事当局出于备战需要,确实压制过相当数量的言论和报纸。林肯甚至命令用军事审判庭——而非普通法院——来审判出版公司。但和20世纪的系统压制相比,这些限制性措施显得微不足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热爱民法,对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感兴趣,请关注并支持“德国民法典学习小组”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德国民法典学习小组” 或者搜索微信号“BGB-ChinaStudyGroup”订阅);并请转发给您的同学、朋友、同事等,及在朋友圈分享,谢谢!有兴趣加入本学习小组微信群的朋友,可先添加该群管理员微信“baiyuanzhiwang”。如果您有好文章和素材愿与分享,请电邮至:joe.wang061110@gmail.com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