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如构成作品,其著作权应当归属于人工智能开发者还是利用者,理论和实务界存在巨大争议。我个人是‘人工智能创作工具论’的提倡者和捍卫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李扬教授表示,“人工智能创作工具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工智能本质上不过是人利用来减轻自己创作劳动的工具,即计算机程序。人工智能按照人的命令和意志输出的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如构成作品,其权利如何归属,充分发挥现行著作权法对科技革命的回应性,利用现行著作权法关于作品构成要件及其著作权归属的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即可,尚无需创设新规则进行立法回应的必要性。理由在于,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上的著作权法所造成的冲击,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诠释著作权法。非人工智能时代,作品创作虽借助了技术的力量,但主要还是依赖人的智力投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人的创作活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主要依赖人的自然智力投入的状态。人与其他物种本质区别之一在于,人拥有意识,会思维,而且意识和思维在不断进步。为了减轻创作的艰辛和投入,人发明人工智能进行创作,使创作变得简单和高效,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就像人发明机械替代人从事繁重的生产活动,减轻体力劳动一样。面对这样一个态势,如果再固守建立在非人工智能时代基础上的著作权法的概念和逻辑,对“创作”进行诠释时,要求思想百分百的表达都必须与人的自由意志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必然关系,显然是落后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应该被抛弃的过气观点和立场。”
相反,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拥抱人发明创作型人工智能并利用创作型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时代的到来,并在此基础上对著作权法中的概念和规则进行全新的解释。以“创作”“作品”而论,考虑到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利用创作型人工智能进行创作且时有侵害行为发生的不可逆转的现实,或许可以采取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将“创作”解释为直接或者间接产生作品的活动,将“作品”解释为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不再过多纠缠于人的自由意志和客观表达之间神秘莫测的百分之百的必然联系,而将关注点聚焦于如何通过运用独创性、损害赔偿、停止侵害、举证责任等法律工具,调节可能因为创作型人工智能被利用来进行创作而带来的作品井喷所造成的反公地悲剧现象,以及可能因大量著作权纠纷案件涌入法院而使法院不堪重负的现象。如此考虑,不仅仅是因为新技术革命的驱动使然,也是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客观需要。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创作被少数人垄断,文化艺术市场被少数资本独占,普通大众难以享受所谓高端文化艺术品的时代必须被彻底打破,历史上一直被认为属于阳春白雪的所谓文化必须走向下里巴人的民间,真正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艺术不应当再成为奢侈品,也不可能再成为奢侈品,相反应当成为热闹集市上人人可得手的萝卜白菜。人工智能时代,人人都有权利成为文学家艺术家,实现非人工智能时代儿时的梦想。固守非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法的逻辑诠释“创作”“作品”等概念,不承认人设定最初关键词和修改关键词利用人工智能输出的表达是作品,不享有著作权的立场,除了反映出面对文学艺术创作被精致利己主义者把持乃至被垄断的顺从立场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尊敬和神化之处。
此外,将人工智能解释为人的创作工具,和著作权法关于雇用作品作者的规定,逻辑上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在雇佣作品情形,雇主的自由意志显然并未直接地、百分之百地决定表达的每一个方面,但有些国家的著作权法规定雇主就是作者或者视为作者,且享有所有的著作权人格权和著作权财产权。这里面的逻辑,就是将雇员视为了雇主的创作手足,或者说创作工具。雇员都可以被人为创设的著作权法规定为雇主的创作工具,为什么将尚无任何自由意志的人工智能解释为人的创作工具,就无法被接受呢?也应当注意到,少数学者一直在鼓吹,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理论体系,可是为什么仅仅遇到人工智能对著作权法规定的“创作”“作品”等概念造成的冲击这样一些并不算革命性的问题,就自主意识全无,而照搬照抄美国版权局的看法,对英国著作权法将计算机程序创作的作品规定为利用者创作的作品视而不见,尤其是无视国内产业,特别是普通民众对于文化平等和自由的需求,来混淆视听呢?
关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的归属,李扬教授认为,如果无合同特别约定,应当属于人工智能利用者,而非开发者。同时,我个人并不赞成某些人工智能开发者通过合同约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属于开发者。人工智能开发者除了可以申请专利外,还可以将人工智能给使用者使用,收取使用费,从而确保收回投资。通过合同约定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所有知识产权约定归属于开发者,将严重影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利用市场,反而不利于人工智能的推广应用,最终于人工智能开发者不利。
同样道理,向人工智能发出提示词,要求人工智能完成特定任务的使用者也不能凭借其自由意志,决定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因此不能认为该使用者从事了作品的“创作”。虽然用户的提示词划定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方向和领域,也可以从人工智能生成的众多内容中挑选出满意的部分,但不能直接决定构成内容的表达性要素。向十套不同的人工智能绘图程序输入同一套提示词,十套不同的人工智能绘图程序将返回内容差异极大的十幅构图,这说明用户不可能通过提示词“直接产生”由此生成的艺术造型,怎么能说是用户通过输入同一套提示词“创作”了十幅“作品”?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同一名美术老师向十名同学发出一套相同的绘图要求,这十名同学严格遵循相同的要求完成的十幅内容差异极大的绘画,岂不就都成了这名美术老师以这十名学生为“工具”而“创作”的作品了?如果认为用户基于人工智能最初生成的画面不断发出修改和调整的提示词,就是在以人工智能为“工具”“创作”最终形成的画面,按同一逻辑,美术老师基于学生根据其最初要求绘制的初稿,不断向这名学生发出修改和调整的要求,那么学生最终完成的绘画,就是美术老师以学生为“工具”而“创作”的作品了?那么所有硕博学位论文是否只要经过了导师从确定题目到修改内容的多次、详细指导,就成了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以博士生、硕士生为“工具”而“创作”的作品?
美国版权局发布的《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登记指南》提出:“当人工智能技术仅从一个人那里收到了一条指令,并作为回应生成了复杂的文字、视听或音乐成果,则‘传统的创作因素’是由技术而不是由人类用户所决定和执行的。......根据本局对现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解,用户对系统如何阐释指令和生成内容并未运用最终的创造性控制力。......是机器决定了如何在输出结果中执行这些指令。......当人工智能技术决定了其输出结果的表达性因素时,由此产生的内容并不是人类创作的结果。因此该材料并不受版权保护,必须在申请登记时声明排除(出登记范围)。”在“《太空歌舞院》作品登记案”中,人工智能绘图程序通过至少624次提示词的输入才形成了名为《太空歌舞院》的一幅画,该画获得艺术大奖,但美国版权局拒绝了将此画作为作品登记的申请,其根本原因在于用户不能通过输入提示词而“实际形成”画面,缺乏对画面的“最终创造性控制”。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宋健表示,首先,北互就该案裁判的探索非常有意义,使得AIGC的定性由学术讨论上升为司法裁判的选择,并促使讨论进一步深化。但由于AIGC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目前全球都在审慎讨论之中,因而观点有分歧也很正常。值得注意的是,该案裁判理由中尽管强调AIGC仍然是人类利用工具进行创作,并强调人类技术的发展带来创作手段的变化和进步,但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大的颠覆式创新的技术变革,一方面使得AIGC生成物极为海量且源源不断,另一方面AIGC生成的图片,完全系通过参数的设置和调整、提示词以及反向提示词的设置等实现的,尽管最终呈现需要进行不断的设定和选择,但最终生成物仍是由AI自主完成的,远超传统“工具论”背景下自然人对机器创作工具的使用方式。由此,AIGC似乎定义为数字产品更为妥当。
尤其需注意的是,从案件查明事实看,目前网上对AI生成的图片是明确以“AI图片”标注并明码标价的,这说明对于AIGC不同于传统自然人的创作,行业的认知是清晰的。进一步,当图片可以利用AI大模型大量呈现时,人类还有没有必要延续传统绘画技艺的长期学习和训练,还是就此灭绝,这是非常值得思考和追问的。传统美术作品的创作,需要自然人对传统绘画技艺的长期学习和训练,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将每时每刻“吐出”巨量甚至不计其数的AI图片时,传统自然人直接创作的美术作品应当更为稀缺和昂贵才具有合理性,因此AIGC将随着技术的迭代变得更为廉价。鉴于此,著作权法是否还是适合的法律调整工具需要审慎讨论。也许将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创作与AIGC加以分割,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更为合理,即传统的自然人创作仍归于著作法保护,如果AIGC需要保护的话,则可以考虑另行制定相关数字产品的专门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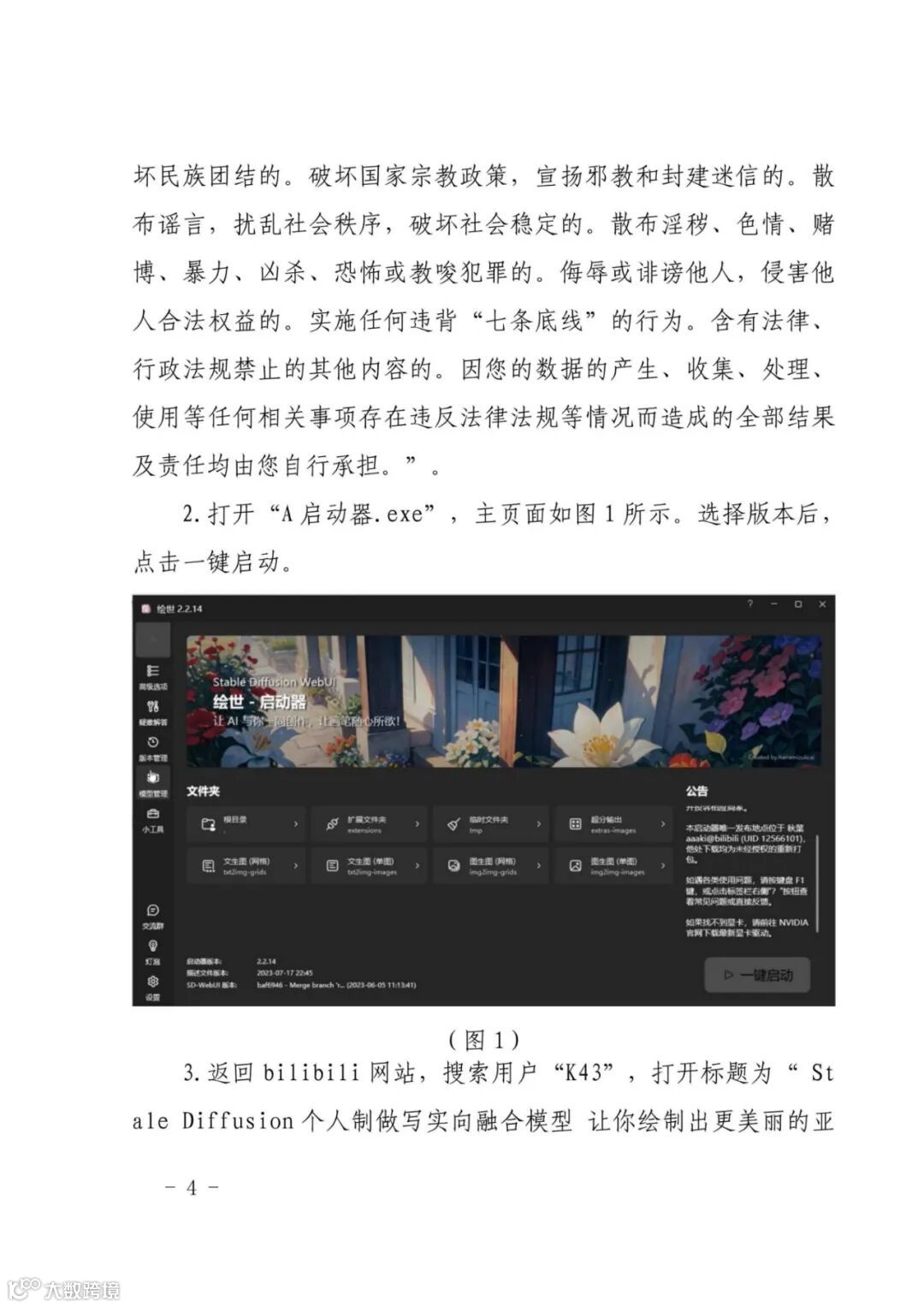






















信息来源:知产财经


